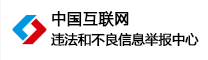- 陕西女诗人群落调查:从来非名士只诉心头一片痴
-
和谐陕西网 http://www.hxsx.net
来源:华商报
2011-03-27 20:27
浏览:
字体:大 中 小
在陕西的创作队伍中,一直有一个被忽略的群体,或许,她们从来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过,于是没有人看到她们身上的共性,无论称她们为女诗人还是女性诗歌爱好者,都不可抹杀她们身上的诗性。
记者走访了西安多位女诗人和女性诗歌爱好者,邀请她们参与到此次调查之中,并回答调查问卷上的问题,为读者捡起散落在三秦大地上的诗歌芳华。
在陕西诗坛,她们寥若晨星,在生活中,她们隐藏着诗人的身份……
她们人数少 影响小
如果要从陕西浩浩荡荡的文学创作队伍中,拎出几位可以用“著名”形容的作家,是轻而易举的事,但如果“著名”二字后换成女诗人,恐怕大多数人要犯难了。伊沙最近在编一本《陕西诗选》,被他收入其中的女诗人有刘亚丽、杨莹、横行胭脂、李小洛、惠诗钦、高灿等六位。
他说:“不能怪我选得少,是人口基数太少,写作的人太少,陕西女诗人写作整体状况比较弱,我不能为了选女性就把标准降低。”
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陕西诗坛的女诗人胡香,曾经在媒体工作多年,较为了解陕西女诗人状况,她介绍,陕西籍女诗人目前活跃并为人们熟知的有刘亚丽、南嫫、杨莹、吕布布、李小洛、三色堇、商臻、崔彦、蒋书平、白芳芳、马丽娜、刘欢、穆蕾蕾、闻方等,从人数和创作阵容上都要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和强许多,尤其是网络兴起后,给女性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。
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梅绍静、刘亚丽,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刘亚丽的诗,那时女诗人很少,她和陕北一批优秀的男诗人如阎安、李岩、远村、尚飞鹏、尚飞林等的名字经常一起出现在文学刊物上,诗评家沈奇称她‘大家闺秀’。另一个是南嫫,她是另一种气质的女诗人,都市气息、现代气息很浓郁,富有传奇色彩,才华横溢,具有多方面才能。八九十年代在陕西诗歌界很有影响,被诗评家沈奇称作‘冷箭’,目前在北京发展。她的诗冷静、准确、犀利,读时有一种很深入的灵魂被敲击的感觉,甚至让人不由自主想回避,就像不敢对视一双太犀利的眼睛一样。”胡香说。
目前居住在安康的李小洛是陕西女诗人中佼佼者,她200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,曾参加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,并获得过“新世纪十佳女诗人”称号,她在梳理陕西女诗人现状时说:“刘亚丽、杨莹、横行胭脂、三色堇、郦楹、宁颖芳她们都是很好的女诗人。只是从全省的整体数量上来看,女诗人似乎还可以更多些。”
一位居住在临潼的女教师写诗多年,笔名“横行胭脂”,近几年知名度较高,她觉得目前陕西女诗人还没有集结起来,而是一种零星分布的状态。“文学是孤独的,确实需要独立,甚至远离一些喧嚣,但文学又是需要一些竞争和促进的,如果陕西女诗人们能有一个圈子,也很好。比如陕西男诗人伊沙他们的圈子令人羡慕,常在一起交流交流,是氛围,也是拓展。另外从我最近几年观察陕西女诗人在诗坛的作为方面来看,能造成一种持久的冲击力的现象还未出现。”
在陕西所有的公开诗歌活动中,几乎都能看到崔彦,她在编辑一份名为《西部诗刊》的杂志,在文学杂志市场萎靡的状态下,这份诗刊只能给小圈子朋友传阅,几乎没有经济收益。她约稿时发现,很多女性诗歌作者居无定所,生存状态并不好。
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当诗人
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之为诗人?这个问题没有答案,世俗的概念将出过诗集的女性诗歌爱好者,称为女诗人,但在采访和调查中,记者发现,这些女性的诗歌写作者几乎都有一个雷同的观点:“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诗人。”
对“诗人”身份几乎都持否定态度
49岁的三色堇直言:“我说实话,我从来没把自己当诗人,就是爱好,就像害了病,已经喜欢、已经习惯。”
郦楹(笔名)在银行任职,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她将写诗定位为一种休闲方式:“有些人更愿意把空闲时间用来唱歌逛街,写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消闲,可以安心去享受写作过程。但是我不会告诉单位的人我在写诗。”“我不是什么作家,也不是什么诗人,只是一个平凡的记录者,记录自己身边的动态和世事的变迁,把它提高到审美的范畴,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感悟和启迪而已。”崔彦这样说。
在记者见到的这几位女性诗歌写作者当中,对“诗人”这一身份几乎都持否定态度,杨莹说,诗人是伟大的、尊贵的,她不认为自己是诗人,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普通诗歌爱好者。
避免社会误解隐藏诗人身份
然而,她们不愿向外界宣称“诗人”身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:社会的误解。在很多人心目中,诗人往往与“另类”、“神经质”、“疯狂”等词汇联系在一起,在陕西女诗人中,这一困惑依然存在。
不论是横行胭脂、还是郦楹,在单位,她们的身份分别是学生的老师、银行的职员,不会轻易将自己的“诗人”身份示人。
郦楹说:“我们怕别人以为我是‘神经病’,其实写诗的人只是看问题更到位,比较感性,比较直接而已。”
对这个问题的思考,李小洛更为诗性:“我想说女诗人就是普通女性,女诗人和普通女性没什么区别。其次,每一个女人都是女诗人。因为女人和诗歌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种隐秘关系。每一个女人都是‘为了看看太阳,才来到这世上’。”
她们和所有普通女性一样相夫教子,一样要照顾一家老小的吃穿住行,在单位仍然要忙于工作,许多的社会角色决定了,女性诗歌写作者在更多层面上,依然是普通女性。
她们极度坚强、极度脆弱,她们是三毛、是翟永明、是舒婷……
别人看见了一 我们看见了三
几乎在所有人眼中,女诗人都与普通女性完全不同,她们细腻、敏感、特立独行、极度坚强或者极度脆弱,比女人更女人,比男人更男人,她们能像三毛一样行走世界,也能像翟永明那样开间酒吧,在城市一隅广交朋友,或者,像舒婷那样,爱得深沉,又隐于无形。
刘亚丽认为她跟普通女性没什么区别,如果非要说区别,在于普通女性没有用分行的文字记录自己的思想和发现。李小洛说,女诗人很平常,写诗和她生活中任何一个别的爱好并无差异。
但写诗却给她们带来了普通女性所没有的收获,细腻敏锐自不必说,不断地思考学习,让她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,分析与判断事物拥有了别样的眼光,刘亚丽认为做诗人的好处在于,面对自身和世界,别人看见了一,诗人就能看见二、三,或者更多,看见了比这个世界更高更远的事情,看见了事物里面和背后的东西。诗让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她说自己的诗歌好比一幅刺绣,“一次大扫除之后家的明窗净几和温馨安谧,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午餐,家人当然欣然笑纳,照单全收了”。
“写作使我多了一部分生活,一部分隐秘的生活。那些积淀的隐秘的孤独,不安,寻求,都爆发出来,生活的体积秘密地增大了。诗歌,把我从一个幼稚单薄的女子解救成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女人,活着,并且坚定地追求一个诗人的名分。”横行胭脂说。横行胭脂的丈夫和女儿是她的读者,女儿受她影响也开始写诗,2007年她生病三个月,女儿躺在病床边写了一首诗《种一个妈妈》,这首诗写出来一个小时后就被刊物编辑拿走刊发。
刚结婚时候,杨莹的丈夫对她说了这样的话:“你写的那诗5分钱都不值。”他们也为此吵过架。孩子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,问她:“妈,你看你写诗吧,有时还没人给你钱,你多写点挣钱的文字。你写那干啥啊?那么辛苦……”但是,坚持多年后,她的家人知道写诗能让她快乐,也就给予了更多理解。
当男诗人的名字在排行榜上熠熠生辉时,她们除却诗人还要做母亲、妻子、女儿……
做女人和做诗人冲突吗?
在中国当下,优秀的男诗人的名字在各种排行榜上熠熠生辉,比如于坚、雷平阳、伊沙、沈浩波、朵渔、桑克等,但能被人们记住的女诗人名字,除了成名较早的舒婷外,就只有翟永明、王小妮等个别几位了。这一现象由来已久,但女诗人们对此的看法却迥异。
正方:杨莹、胡香、崔彦
观点:
女性感情细腻但生活会淡化诗意
在写作上,没有人可以忽略女性写作的力度,但是母亲、妻子、女儿是女性难以摆脱的社会角色,虽然所有人都不承认女诗人在创作中弱于男诗人,但有一部分女诗人认为,女诗人目前影响力小的原因是由于女诗人作为女性,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带来的任务,例如,母亲、妻子、女儿,家庭琐事会淡化诗意。
杨莹:这与她们的生理、社会角色不无关系,她们总是顾及家庭幸福,常常生活第一,写诗第二,每个女人都要照顾孩子,赡养老人,比男人承担更多家庭事务。然而她们的潜意识发达,情感力量深厚,这是她们的优势,如果能很好地保留女性的特质,而且把它很好地转移到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去,是美而有力的。
胡香: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仍受男权思想影响,她首先是一个母亲、妻子、女儿、媳妇以及工作者,等等,是从属性角色,这些角色扮演得好不好,成不成功是重要的,是社会考察一个女人的重要项目和指标,而她的内心需求,精神追求和需要,却往往被忽略,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,是离经叛道和出格,除非做得非常成功,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,这就限制了大多数女性在这方面的自由发展。而男性相对要好得多,很少会有这方面的困扰。
崔彦:她们不但要承担社会事务还要承担家务劳动。我上有父母需要照顾,下有儿女需要抚养,每天忙碌穿梭在人群车马拥挤的街头,求生之重,迫在眉睫,没有一天有过享受、休闲、偷懒的想法。从主观上来说女诗人的视野没有男性开阔,认识世界也没有男性深刻,细腻的柔情的感悟多些,理性的、哲意的认知少一些。
反方:三色堇、刘亚丽
观点:
生活体验给女性更多诗意
郦楹、三色堇:女性诗歌写作者更多的是在默默写作而已,对诗歌的追求只在于记录和抒发,发表、获奖等均淡出她们的视线,于是造成女性诗歌“虚假弱势”的局面。在以下几位看来,女性社会角色的丰富,反而拉近了女性与诗歌的距离,让她们有了比男性更丰富的生活体验。
横行胭脂:女性比男性多了生育体验,女性对世界的感知,应该像生育一样,更敏感,更热烈,更疼痛才是,女性“雌声”之美,也应该是她们的优势。对女诗人式微这一说,我觉得应该是女性思考问题的方式影响了写作的质量,女诗人都比较感性一些。
刘亚丽:一个写诗的女性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、普通的女人,然后才是一个诗人。诗人只有先做了普通人以后,才会专注和尊重普通俗常的事物,并在其中发现诗意。诗歌的品相和质地更接近于女性。我从不认为女诗人在创作上弱于男诗人,相反绝对强于男诗人。
男诗人PK女诗人
观点:
女人的诗男人写不出来
相反亦然
李小洛:男女诗歌不存在强弱,只存在差异。诗歌是一种历史心灵的呈现。在女诗人的作品里,我们应该观察到时代所赋予我们“女人”的种种生活和心灵遭遇。男女更大的不同之处我想还在于男诗人们是在抵抗,而女诗人们在承受,不论怎么否定,怎么去避免,这种上天所赋予的性别差异和文化驯养还是让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诗歌有着区别。从这一点上,性别经验和性别差异还是与诗歌有着必然的关联,可以说,女人们写的诗男人们写不出来,相反亦然。
胡香:翟永明、阿赫玛托娃、吉皮乌斯、茨维塔耶娃、米斯特拉尔、西尔维娅、萨福、李清照等等,她们一点也不弱于男诗人,只是在整体上,在数量上,处于弱势,这跟千百年来男权统治和思想的影响有关,从智力和精神追求、精神生命的质量上来说,女性和男性没有谁强谁弱的差别,有的只是个体差异。
横行胭脂:女性诗歌都显得比较轻灵,质地不如男性诗歌那么厚重。女诗人对于地域情感的捕捉以及对于思想深层的触摸还比较弱。
男诗人眼中的女诗人:
一旦写纯粹了男诗人无法企及
在女性诗歌写作者眼中,男诗人占据了诗歌星空的中心,他们的光环遮盖了闪耀异彩的女性诗歌,男诗人有江湖,有义气,女诗人往往被游离在这个环境之外。
陕西诗人伊沙强调一句话,文学的标准是不分男女、一视同仁的。他认为女性诗歌写作者目前的这种现状,和女性自身对自身的定位有关,从地域上说,陕西女诗人没有四川、重庆、东北等地的女诗人活跃。“她们往往承认这就是个男权社会,绝大多数女诗人受困于角色,往往放弃了文学应该承担的东西,或许是性别局限,或者是对社会的漠视,她们在沉默中接受了社会定位的边缘角色,而不是反抗去承担更多角色。女性更多允许自己写写小情调、人生感喟,自己在文学中往后退。但男诗人,因为被社会暗示的角色,他们知道大诗人应该做什么,不管能否做到,所以,男性诗人就多一些。”伊沙说。
他认为女性应该承担更多题材,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,能够写透生命,例如翟永明,只要发挥自己的特点,女诗人一旦写纯粹了,男诗人反而无法企及。本报记者狄蕊红
- 相关文章
- 一位患者致长安医院骨科医护人员的感谢信
- 蒋峰作品集捐赠暨蒋峰文学基金成立仪式在西安举行(图)
- 国医仲景(西安)体验中心走进古槐养老院探望老年朋友
- “关中红冬枣酒"横空出世 为酒类消费结构再创辉煌
- 榆阳区崇文路街道寨城庄社区开展“聚民心 除陋习”道德评
- 国医仲景“艾灸之家”在陕西稳步发展
- “华山论检”——邮政业智能安检系统成果交流会在西安举行
- 首批100台全智能艾灸沙发公益投放走进临潼古槐养老院
- 首批100台全智能艾灸沙发公益投放4月9日将走进临潼
- 田宁:从厨师蜕变为世界健美冠军
- 爱国企业家医学家齐英翔:中医瑰宝亟待发扬光大
- 好一朵盛开的兰花——82岁老人为他写了一首歌
- 打造“5A”级慈善组织 发挥“红凤工程”品牌效应
- 让读者体验文学的数字化场景 司辰携《命运乐章》西安会读
- 和谐声明
-
和谐陕西网(陕西和谐网)——文化与公益的践行者。我们不做新闻,只传递资讯、记录生活。请完整转载,切勿断章取义,载时请注明"来源:和谐陕西网hxsx.net"。和谐陕西网转载其它媒体和网站的图文资讯,不代表本网的立场和观点,不对其真实性负责。若因内容、版权或其它问题需要修改或删除,请与编辑部联系630990995@qq.com。